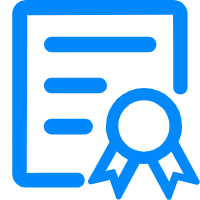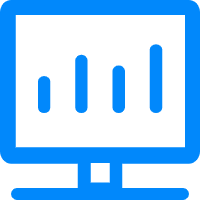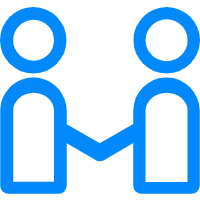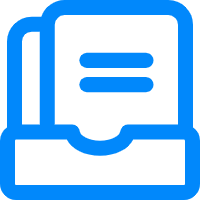在北方一座老工业城市,周师傅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。这位54岁的焊工已在钢构厂干了整整三十年,手艺精湛,连厂里最难啃的活儿都得靠他。202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,厂里赶制一批出口订单,周师傅像往常一样戴上护目镜,点燃焊枪,开始一天的工作。然而,谁也没料到,这一天会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。
焊接过程中,一块悬挂的钢板突然松动,砸向周师傅的左腿。剧烈的疼痛让他当场倒地,工友们手忙脚乱地将他送往医院。诊断结果如晴天霹雳:左腿胫骨粉碎性骨折,伴随神经损伤,医生坦言,即便康复,也难以恢复正常行走能力。周师傅的妻子哭着说:“他这辈子就靠这双手一双腿吃饭,现在怎么办?”
事故发生后,周师傅向厂里提出了工伤赔偿申请。然而,厂方却以“钢板松动属不可抗力”为由,仅支付了部分医疗费,拒绝承担后续赔偿责任。面对一家人的生计压力,周师傅决定提起诉讼。这场老焊工与企业的对峙,就此展开。
赔偿的起点:工伤认定的既定事实
幸运的是,事故发生后,周师傅的工伤认定申请很快得到了当地人社部门的批准。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,他在工作时间、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伤,毫无疑问属于工伤。厂方对此并无异议,但争议的焦点迅速转向了赔偿金额。厂里主张仅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医疗费,而周师傅的律师赵丽则认为,他有权获得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,甚至可能涉及停工留薪期的工资。
赵丽在法庭上拿出了周师傅的病例和职业病史,强调他因长期焊接导致的肺部轻微损伤,此次事故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健康危机。她援引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七条和第三十七条,指出周师傅的伤残等级应评定为七级以上,企业必须承担相应赔偿。然而,厂方代理人却辩称,周师傅年近退休,伤残对其就业影响有限,赔偿应“适度压缩”。
企业的辩护:成本与责任的博弈
庭审中,厂方的态度令人意外。他们提交了一份内部调查报告,称钢板松动是“吊装设备老化导致的突发故障”,试图将责任推给设备供应商。同时,他们还出示了周师傅签字的安全责任协议,声称他曾承诺对个人操作安全负责。厂方律师冷冷地说:“周师傅是老员工,应该预见到风险,他的疏忽才是事故主因。”
赵丽当即反击:“这份协议明显是格式条款,违反《劳动合同法》关于公平性的规定,不能作为免责依据。”她还调取了厂里的设备维护记录,发现吊装设备已有三年未检修,远超安全标准。法官听罢,眉头紧锁,要求厂方补充提交设备采购和维护的完整证据。然而,厂方的回答支支吾吾,显然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明。
正义的落槌:老焊工的坚持
经过三次开庭,2025年2月,法院终于作出判决。结合周师傅的伤残鉴定结果,他的伤残等级被评定为七级。法院认定,厂方在设备管理和安全保障上存在重大过失,需支付周师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8万元、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5万元、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8万元,以及停工留薪期工资共计10万元,总额超过40万元。
判决宣读时,周师傅坐在轮椅上,双手紧握拐杖。他没有流泪,只是轻声对赵丽说:“这钱不是白拿的,是我三十年焊花换来的。”厂方虽不服判决,却因证据不足未提起上诉。此后,厂里悄然更换了一批老旧设备,但周师傅知道,自己再也回不到那个熟悉的车间了。
故事的余音
周师傅的案子在厂里传开,有人说他“运气好”,也有人感慨他“太倔”。但在法律的视角下,这不仅是一场赔偿之争,更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对尊严的坚守。工伤赔偿的数字背后,是无数像周师傅一样的工人,用汗水和伤痛书写的故事。或许,这场无声对峙,能让更多人听见他们的声音。